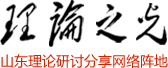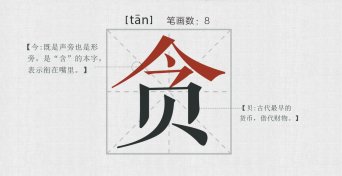德法合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
作者: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 陈雅丽、 上海大学法学院 潘传表
历史上的王朝,能够做到隆礼重法、德法合治的,大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可以说,德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与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历史上德法合治中的法治是古代法家的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同样离不开道德的评判和支撑,同样需要德治的价值引领和手段配合。传统德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路径时,要取其精华,做好转化和创新。
为法治之法提供合法性判断
法治强调法律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服从。亚里士多德说,被人们普遍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那么,人们服从法律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如何判断良法?实际上,这些疑问都是人们对法治之法合法性的追问。而法治理论本身是难以回答这个合法性追问的,必须由法治之外的理论来提供回答。而在传统德治思想中,主要由儒家阐发的“德”恰是一种有着精致而丰富内涵的合法性思想,它能被用来判定和说明法治之法的合法性。法律之所以有效力,不仅仅因为它们是按法定程序和权限制定颁布的,更是因为这些法律符合“德性”的要求,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拥护,为人心所向往。儒家的 “德性”标准是多重的,是复合的,而且彼此之间又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以德配天”要求统治者正己修德,顺天应人,敬天保民,是一种神圣合法性要求;德政仁政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赋税,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做出现实的功业和政绩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是一种民意合法性要求;德化天下要求统治者修文德、兴教化,对华夏文明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传承与更新,是一种文化合法性要求。这三重合法性之间相互牵制,可避免政治和法律运行过程只执一端、不顾其余,最能体现中国文化追求“中和”的精神。
上述“德性”标准强调民意民心,要求政治和法律满足民众的私欲和功利的要求,但是,决不仅以此为限,崇高的道德追求、远大的文化理想、国家和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更是政治和法律要追求和保障的。如果我们吸纳和借鉴传统“德性”标准为当代法治之法提供合法性判断的话,则将使我们的法律有了灵魂,有了锚点,有助于我们匡正法治之法的偏失,引导现有制度向更理想境界靠近。
德润人心是法安天下的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是个体利益和社会秩序最可信赖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法律并不调整人的内心。然而,人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物质欲望的生命,也需要精神、文化和信仰。一个内心失范的人,法律再严密,也难以约束他的外在言行。同样,一个国家或民族,也必须稳固其主体文化或信仰,否则国家和民族必不稳不安,甚至将分裂。德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的问题,包括如何提升社会道德。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来安顿人们的身心,辅以规范人们行为的外在法律规范,是标本兼治的策略。
中国传统文化把“德”阐释为制定和评判政治和法律的一种内在价值或超越原则;德是对个体“心”、“性”的发掘和弘扬,要求尽心尽性求诸己,既是为己,又是为国为民,乃至为天;德从个体出发,推己及人,但又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对个体理性的超越,发自个体又超越自我。德要求个体将其欲望及利益与他人、群体及自然统一起来,和谐共容,而不是对立对抗,最终达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此外,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人身心的安顿并不借助宗教神灵,而是凭借人文哲学的力量。从个人的修身立德,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安排,都有一套一以贯之的哲学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道理,都蕴含在“德”字之中,强调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这样一套人文哲学,是仁爱的、和平的,更是理性的。
“得人”是法治实施的关键
传统德治思想认为,人的德行和才干对于法的实施效果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不能培养和选拔具备相应德行和才能的人去掌握权力以实施法律,再完善的法律也只会成为摆设,再严密的法律也会处处是漏洞。“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让好人变得更好”。但前提是要让贤者在位。历史上不少改革没有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人的因素上出了问题。德才兼备的人居于高位,不仅可以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起到模范的作用,还能使小人有所忌惮,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君子之德”会影响到“小人之德”,就像风吹到草上,“草上之风,必偃”。
传统德治思想正视人的自然差别对制度实施造成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差异安排。男女老幼、贤愚不肖,这些都是人的自然差别。在选人用人上,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些主张都深刻地洞察了人的差别对制度实施造成的影响。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从人对制度实施的影响角度而言,荀子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德治可弥补法治的形式主义弊病
为了消除法律本身所造成的专横,比如消除那些由于法律的不确定、不公开、不稳定、模糊、溯及既往、内部冲突以及政府凌驾法律之上等原因造成的危险,要求法律具备特定的品德,即遵循富勒所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符合这种“内在道德”的法律称为法治。然而法治本身并不能决定法治之法的实体内容。要防止法治实体内容为恶,则必须依靠法治之外的力量来承担。在这里,传统德治思想正好有其用武之地。
另外,法治形式本身也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需要结合德治加以克服。例如,一方面,法治需要法律必须明确、具体,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防止人的偏私,同时,法治又要求法律不能朝令夕改,保持稳定性,以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形成预期,得以相应地规划和实施自己的行为;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的,立法者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法治又需要法律维持一定的弹性,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动、消除法律适用的僵化。但是在法治的框架内,这两者的要求是不可兼顾的。而德治强调人在制度中的作用,将人作为制度中最重要的变量,在制度中赋予贤人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信赖贤人的经验、智慧及品德。在德治框架内,通过人应对规则僵化的问题,倚重道德来培育良好社会秩序,仰赖贤人弥补制度漏洞,简化规则,提高规则的运行效率。故此,德治与法治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可以将人的治理与规则治理统一起来。
初审编辑:牛乐耕
责任编辑:李士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