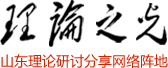清初博学鸿儒群体的心态流变——以李因笃为中心
作者: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代亮
摘要:清初博学鸿儒群体中不乏具有遗民情结者,其心态虽因入京参加考试而发生转变,但并非简单地以“今我”完全代替“故我”,而是呈现出新旧交融并存的特征。其中,李因笃尤具代表性。康熙十七年入京之前,他受外祖家诸长辈的影响,安于穷贱,坚决不仕,行迹与遗民相近。入京后,一方面,由于遗民情结的浓厚,他流露出强烈的思归心理,并积极想法离京;另一方面,由于亲身感受到清廷的眷顾,其对新朝的态度有明显松动,对康熙帝的德业与事功不乏称颂。但他始终坚持不仕,晚年对应征之举亦不无愧疚。二者交织混杂,显现出其后期心态的复杂多元。这一特征,为诸多深具遗民情怀之博学鸿儒所共有,也反映出清廷统治政策调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限度。
关键词:李因笃;博学鸿儒群体;遗民情结;心态流变
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考试所录取的五十名特科进士,人数众多,遭际有异,对清朝的认知并不一致,其中某些人物如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潘耒、严绳孙等人,或 一度投身抗清斗争,或具有一定的遗民情结。关于他们的心态,论者多认为在入京参加考试尤其是授官之后,群体性地转向归附新朝,效忠清帝,却忽略了其心态的复杂与多元。本文拟对上述诸人的心态流变加以探析,以说明清廷统治政策调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限度,具体论述则以李因笃为中心。关于李氏的心态演变,已有论者作了启人心智的探讨 。不过,个体的心理世界往往错综复杂,前后虽或有彰明较著之变异,却很少是简单地以“今我”完全代替“故我”,而是呈现出新旧交融并存的特征。对李因笃在博学鸿儒群体心灵史中的典型意义,以及以他其为代表的博学鸿儒群体心态的递变,仍需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人,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李氏在清初声名籍籍,为三秦士人眉目。其一生行迹,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试后的离京之举最为引人注目。康熙十七年(1678年),李因笃被迫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自入京之日起,他就以母亲老病需要照料为由,屡屡向在朝官员陈述苦衷。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后,他备受时人艳羡,所谓“布衣奏赋,立致清华” 。但他对这份不世之荣无动于衷,伏阙陈情,请求返乡,最终得遂所愿,从此直到离世再未出山。对于其出处始末,史家有论曰:“虽以母志力辞新朝官守,得以放还,然名节终亦不免有亏。”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与其斤斤于辨析李氏的名节是否有亏,不如回到具体的时空场景,还原人物心态流变的过程及原因,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体味“当事人”乃至博学鸿儒群体心理世界的复杂。
一
在康熙十七年被征召入京以前,李因笃受外亲家诸长辈家传遗教的影响,不仕新朝,安于穷贱,具有浓厚的故国情结,与遗民行藏不无接近。其高卓的品节也受到遗民群体的称赏,并被引为同道中人。
李因笃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在外亲家度过,对外亲家诸长辈的立身行事耳濡目染,也为一己的人生路向选择奠定了基石。崇祯七年(1634),李因笃之父李映林病卒,继之关中大乱,农民起义军攻至富平,其祖母杨氏与若干族人“登楼,并焚死。李氏之门合良贱死者八十有一人”,李因笃与母亲“走之外家以免” 。在家庭破败之后,李因笃为外祖父田时需所抚育,并随其读书受学。在外祖父的悉心培养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李因笃幼龄时就已表现出卓荦的文章写作才能,“八岁通制义,濡毫预群贤。……十岁通小论,仞成云台篇”,他又因博学多识而崭露头角,受到地方名流的称赏:“追随侍御宅,习礼叨宾筵。谓我尤强记,藏书腹已穿。诸宾半疑信,即席分彩笺。哦毕贾董策,续宾咏甫田。宾惊起举爵,剩酒沾喉咽。”11岁时他参加县试,并被拔置第一,“始试崔明府,虚声自此传” 。但就在他个人渐欲成立的关头,明室大厦已近倾覆。他的外伯祖田时震和外祖田时需兄弟对明廷忠心耿耿,前者“授以伪职,不屈死” ,后者“内明外刚,临难不夺,遭闯乱,力拒伪命,弃诸生” 。田氏昆仲的忠孝节义之举,无疑为后辈树立了标杆。此时的李因笃,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长辈的言行举动应当有亲切感知,受其影响自是顺理成章。另外,田时需在明室覆亡、外族入关后,不以功名利禄为意,隐居田园,坚决不仕,并且教导外孙安于困顿的生活,以修德进业为急务:“世俗所矜爱,尝思其飞骞。惟翁著隐德,教我安胼胝。困学虽难就,潜修庶苟全。双丸互驰逐,问序何乃遄。勿论忍终寠,泥途嗟蜿蜒。总教足蔬食,粗绤聊蔽孱。”李因笃后来不负田氏所望,安于穷困,沉浸于经史之学的研讨,以诗古文创作为乐事,同诗中他感喟道:“谁与寄斯信,达之于九渊。得翁舒积抱,欢笑比当年。” 尤可窥见他对田氏教诲的持守之坚定,以及二者人生价值观的一脉相承之迹。另外,李因笃“自早年受知于母姨夫焦公二虞先生,谬以有道期之”,而焦氏在易代后隐居不出,躬耕田亩,坚决不与显贵交接:“考槃高节晚逾贞,迟暮力田亦薄获。显者到门每辞谢,狂夫执手情开辟。”康熙十六年,李因笃探望焦氏,两人深谈不倦。上引李氏诗中又有曰:“始知所亲即所宗,相见今夕为何夕。” 奉姨夫焦氏为“所宗”,可见其人生价值观也受到后者的熏陶。
李因笃11岁为庠生,13岁时成为廪生,同年明朝灭亡。他的祖上既非明朝官员,本人也没有获得正式功名,“诸生于君恩尚轻,无必不应试之理。使事势可已则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则亦不妨委蛇其间” 。但在被迫应征之前,李因笃从未主动选择这条道路。他“年三十,弃诸生” ,已然断绝了出仕的念头,也表明了对清廷的疏离。这一心态在诗作中时有流露。《土壕有坊题云苏季子故居》云:“七国雄长在,苏君自绝伦。野荒函谷雨,山护土壕春。帚篲移前路,轮蹄满后尘。宁知东蹈日,别有拒秦人。” 以苏秦的“拒秦”之举自勉,拒斥新朝之意溢于言外。非独诗歌创作如此,即便在诗学批评中,李因笃也念念不忘发挥此义,将遗民情怀暗寓其中。朱彝尊《王崇安诗序》记李氏评论秦地诗风之语曰:“吾秦,周之旧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才三十一,非产于周者乎?降而《秦风》,于《车邻》侈车马侍御之好,于《驷驖》有田狩园囿之乐,于《小戎》、《无衣》美甲兵矛戟之备。若似乎成周之遗俗,一变而为无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盖言洛也。‘所谓伊人’,则东迁之主也。‘溯洄’、‘溯游’,缠绵悱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来季子叹其为夏声焉。” 对《秦风》中的《小戎》等篇章好感无多,而对《蒹葭》则情有独钟,目为“夏声”。盖前者不过称颂形容,而后者则有“情深故主之思”,与其心理世界暗合。他在诗中称颂那些心系前朝的友人,如《扶风行赠王九青太史》有曰:“浪游南北不称意,霜雪忽盈颠毛脱。西抱遗经归汉宫,面颜憔悴志莫夺。有时独步二京道,怀古狂吟天地豁。” 赞誉对方尽管年龄老大,生活穷苦,仍然不忘前朝,在“怀古狂吟”中自得其乐。这何尝又不是他本人的写照呢。也正是出于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以伯夷、颜渊一类人物作为典范:“夷渊称至德,陋巷饿岩幽。养晦道所贵,期君追前修。” 虽是对友人的期待,实是夫子自道。他又向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君看五柳公,自寓桃源记。幸托素心侣,何辞终夕醉。” 钦慕物外之乐,在与若干“素心”同道的唱酬往来中自得其趣,将功名之想抛掷脑后。关于这一点,他的贰臣友人曹溶曾有评说:“怀中一掬遗民泪,物外千年处士庐。” 可谓洞中窾要。也正因此,他与若干遗民不乏同道之感,并被后者引为莫逆。
李因笃与新朝官员和遗民均有往来,“圭组之英,蓬荜之彦,俱与交欢”,而若论彼此心曲之相通,与其“尤以古道相底厉” 的遗民群体无疑才是知己。其遗民友人,除了陕西当地的李颙、王弘撰外,还有顾炎武、傅山、屈大均等,他们谈道论学,频频唱酬。其出色的文学才能和卓特的道德品节,均为友人所击节称赏。李颙曾向友人直言李因笃“风雅独步,气谊过人” ,“气谊”云云,大概正是有见于后者的遗民品格。王弘撰对李因笃入清后的放弃诸生资格之举啧啧称叹,有“察其行谊,岂今人中所易得者” 之评。顾炎武对李因笃也屡有称誉,在时人眼中,顾炎武“论交甚严,有议其太峻者” ,但他对李氏则不吝赞词,与其唱酬之作不一而足,赏叹之意时时见于笔触。康熙十六年(1677年),顾炎武再至陕西,所作《过李子德》诗有云:“相看仍慰藉,均不负平生。” “不负平生”,当指彼此遗民立场的坚如磐石。从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出,李因笃通过自身言行,已然在士林中稳固树立起遗民形象,其心态与一般遗民亦无二致。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康熙十七年的被迫应召,他的后半生大概会波澜不惊,一如既往地与友人唱酬赠答,谈艺论学,游览山川风物,也将以“遗民”和“处士”的身份而终老。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清廷统治政策的调整,严峻的人生抉择摆在了年近半百的李因笃面前。
二
李因笃被迫入京后,本于浓厚的遗民情怀,又面临舆论及友朋的强大压力,频频以母亲老病需要照料为由,请求在朝官员建言朝廷以遂归乡心愿,反映出他对清廷的抵拒心态。不过,在居京期间一直到出京返乡后,李因笃对康熙帝屡有赞颂,已然承认了清朝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他对前朝的眷恋之情仍不绝如缕,对自己的行藏出处也时有内疚,又流露出鲜明的遗民底色。两者交融混杂,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
康熙十七年,清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此次征召的范围极为广泛,举凡旧朝遗民、新朝官员以及崚嶒失意的文人等,无不在网罗之列。其实,早在这次下诏之前,李因笃就已为地方主政官员所注意,“军机密议,待决于公者,邮使相闻,络绎不绝”;尽管他后来避居凤翔和延安等地,但仍然为官员的政务咨询所困扰,不遑宁日,致有“名之累人有如此” 的感慨。其友人甚至要向当政者推荐李因笃,经其力辞得免。拒绝地方官府的征聘,难度相对较小;但面对带有强制性的朝廷征召,辞免实属不易。诏书下达之后,李因笃受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及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人联袂举荐。起初他以母亲老病求辞,但并未得到康熙允准。面临着朝廷的巨大压力,兼之母亲田氏“勉令治装” ,他与傅山、王弘撰等人在催促之下,百般无奈地踏上征途。
李因笃的若干友人面对清廷的征举,或坚守立场,不为屈服;或采取柔性抗争的策略,消极应试。前者如顾炎武和李颙都不惜以死抗争,后者如傅山与王弘撰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到京之后或“卧病不起,吏部验实具题,未与试”,或“不出僧寮,不与燕会,不投赠诗文。间有著作,皆寓归兴,即有贵官访者,亦不报谒,命儿子称谢而已” ,最终在考试后不久就得以回籍。他们坚贞不屈的气节广为士林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相反,“诸号为名士,高蹈丘园者,率宛言卑词,望走豪贵之门,伺阍人喜怒以为欣戚” ,则为人齿冷,备受讥刺。其反面警示意义不言而喻。“行百里者半九十”,可以想象,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因笃,若在此时出仕,难免贻时贤和后人以把柄,招致舆论的嘲笑与非议,背负异常沉重的道德压力。其实,李因笃的入京之举,已经招致了友人的不解和责备。此前顾炎武对李氏期待良高,并以他为典范劝诫弟子潘耒的应征:“天生(李因笃)之学,乃是绝尘而奔,吾且瞠乎其后,不意晚季乃有斯人!今虽登名荐剡,料其不出山,更未可知耳。” 所谓“学”,恐怕不仅指学术造诣,还关涉立身行事。不过李因笃毕竟没有顾氏那般坚毅果敢。他甚至还力劝李颙应征,“至訹之以利害”,盖为其身家着想。但此举招致顾炎武的不满,顾氏认为其“必援之(李颙)使同乎已,非改其晚节,则必夭其天年矣” 。动以大义,晓以利害。这未必不是对李因笃的旁敲侧击。而远在岭南的屈大均,闻说李因笃入京后,毫不掩饰其失望之情。《赋寄富平李子》曰:“河华高居早有名,鹤书频使羽毛轻。三秦豪杰哀王猛,一代诗歌恨少卿。绝塞虽将黄鹄返,空山无复白云迎。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目已成。” 以辅佐或投靠外族的王猛与李陵比拟李氏和朱彝尊,对二者的未能坚守立场深表痛惜与不满。征之于李氏的本心与后来行迹,屈氏所论有失于主观。不过,来自舆论的指责以及友人的微词与讥讽,给李因笃的心理负担不言而喻。
李因笃的应试并非出于本愿,入京之后,其遗民本色也一如既往。在与新朝官员的唱酬中,他不失时机地表明意欲归隐的想法。《陈情抵京,再寓张廷尉幼南斋中属书屏诗十首》之十云:“努力济时属公等,茂陵终许卧相如。” 在与应考诸人游赏冯溥的万柳堂时,他有诗曰:“肯赐五株归渭曲,衡门长日带清阴。” 不愿流连京华冠盖,意欲返归田园。这一心绪在与新朝显贵的唱酬中尚显含蓄,而在与遗民同道的交接中则显露无遗。他曾对王弘撰诉说苦恼:“即今长安道,贤达密列仗。底须驱麋鹿,绵蕞议趋抗。偃卧室尝闲,将迎项犹强。” 与奔走逢迎的“贤达”划清界限。诗末两句尤其体现出其铮铮傲骨,以及不欲为朝廷所羁縻的志向。《答无异先生》云:“暗存乔岳泪,犹把汉臣诗。柳自青阳色,松余白雪姿。冥鸿随所往,不图上林枝。” 以坚贞的松柳自喻,心眷故国,坚守华夷之辨,丝毫不贪恋清廷将会给予的荣华富贵。面对顾炎武等人的误会与不解,其《得宁人先生书感赋却寄》直陈心曲:“幽芳出谷原多事,劲竹同根迥自如” ,上句以“幽芳”自比,透露出朝廷强行征召所带来的压力,下句则以“劲竹”自喻,意欲保持高洁的品节,不因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改变,倔强意态即此可见。结合他日后的实际行动来看,李因笃此言决非虚假之词。
入京之后,李因笃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向当道官员频频陈说母亲老病需要照料,期盼对方能建言朝廷批准返乡。朝中重臣如冯溥、叶方蔼、李蔚、杜立德、梁清标、魏象枢等人,为其申说殆遍。《赋赠叶学士讱庵》曰:
当年逢访落,被诏至樵牧。少壮多夸辞,诸公或谬录。虚名玷荐贤,屡檄蒙敦促。扶病哀台司,跽陈许削牍。睿怀自崇广,衔恤空踟蹰。宛转策引迈,粗粮倾储粟。刻归欺老亲,行役浩川陆。……叨恃下交谊,愿抒怀抱曲。圣王体庶物,陟屺为频蹙。喉舌赖良粥,细微原并育。一夫苟失所,如己推沟渎。公肯置飞鵻,籲恩纵野鹿。泰山仰止同,遥庇孤生竹。
极陈自己以“夸辞”而得“虚名”,名实不符,言外之意即是难为朝廷效力。更以启程前对老母承诺“刻归”以及思母心切为由,期盼叶方蔼能向皇帝说情,盼望当政者本着儒家的孝道,将自己放归田园,语气近于哀求。在此诗写作前后,他为清廷录取,与朱彝尊、严绳孙、潘耒三人以“布衣入禁林”,被时人称为“古今旷典” 。但李因笃他对此名号非但不以为荣,反而想方设法加速离京。他向时任内阁大学士的李蔚诉说衷肠:“势迫违慈母,途歧恋别筵。雪霜身契阔,河海泪潺湲。……乞养要无已,孤恩信有焉。回头双华阻,举目五云连。所恃萦瓜瓞,还劳芘葛绵。恭期致尧舜,锡类许矜全。” 不愿恋恋官位,恳求对方能成全自己返乡照顾老母的心愿,诗意与上引致叶方蔼诗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他向理学名臣魏象枢企求援手:“家贫怕不充,乞米负且戴。况乃滞行役,维萱违树背。悠悠忘啮指,孰与救衰惫。公有人伦责,绝裾亮所诫。愿归窃余光,明发自淑艾。” 叶方蔼和李蔚是否为其向康熙求情,难以确考。征诸李氏本人后来的回忆,魏象枢的确曾助其一臂之力。李氏在归乡后作信致魏氏,称其“代为抗疏,高风大义,求诸古人所希” ,其晚年所作《存殁口号一百一首》第一首中“封题义重压弹冠”句下自注云:“大司寇魏公象枢前以御史大夫,为予密疏龥归。” 可见他后来得以获准返乡,与魏氏的襄助密不可分。
李因笃所以急切返乡,除了对母亲的思念与牵挂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意欲保全其遗民志节。关于这一点,时人在其离京时所作送别诗中已有指认 。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后,他随即上书康熙,祈请归养老母,但“通政司不敢以闻” ,并未将其上交康熙。通政司,明代始设,清代沿置,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通政司官员所以不接收其奏疏,盖考试结束仅两月有余,而且李氏甫被授予检讨之职,或有逆龙鳞之虞。李氏“不得已,冒封事上之。帝鉴其诚,许之,不以违制罪也” 。得以不就职而归。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李因笃此举面临极大的人身风险。同为博学鸿儒科进士的徐釚就说:“伏阙再上书,终养遽难遂。封奏假密陈,尔乃达于帝。当宁虽动容,小臣魄犹悸。” 道出了局外人心惊胆战的观感。李因笃对可能面临的后果应当有所估计,而所以毅然不畏,大概只能解读为其遗民立场的坚定使然。
李因笃在居京应考前后,亲身感受到了新朝的礼贤下士。康熙帝对于来京应考者在物质生活上给予诸多优待,在按月拨付银两以供应生活需求外,同时兼有赐宴,极尽笼络之能事。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关怀,使得来京考试的诸多士人心存感念。朱彝尊、毛奇龄等人均有诗文称誉其事。李因笃诗集中对此记载不多,但也有涉及。《陈情后投上家高阳相国》曰:“滥分仓庾米,叨给度支钱。睿藻虽同及,温纶乃下诠。爰忘蓬户陋,竟备石渠员。” 另外,李因笃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名节,的确也离不开康熙的玉成。李因笃对此也心知肚明,其离京之际所作《留别吴侍讲卧山》有曰:“帝性孝且仁,深宫照无忒。怀归悯小臣,念母情凄恻。诘旦沛殊恩,还山忽已得。 赞誉康熙具仁孝之心,而且能推己及人。诗中以“小臣”自称,可见他已认同了清朝的合法性,态度已然软化。此处所以俯首称臣,当然有时间流逝冲淡了遗民情结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亲身感受到康熙的“眷顾”使然。与此同时,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新朝的统治趋于稳定,康熙施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以对汉民族文化的接受为重心,赢得了士林包括遗民在内的高度认肯。李因笃对此屡有赞誉:“更喜右文逢圣主,明良佇和集贤端。” “自昔时艰多右武,于今主圣复崇文。” 对遭逢圣主而欢欣鼓舞,对文治的复兴充满期待。除此之外,李因笃对康熙的政治功绩以及治理方略等,也屡有赞颂。如《方伯穆公廉仁颂并序》曰:“上御极之二十有八年,声教被于万国,自古重译所不至,咸受书朔而通梯航,偃武修文,告成岱宗,而犹宵旰孜孜,殚精吏术。”而且不无感恩地回忆道:“旧岁蒙恩旨,尽蠲陕西田租,秦民击壤康衢,不啻游尧天而载舜日。” 赞誉新朝统治的蒸蒸日上,视其为尧舜再生,夷夏之防的观念几近泯灭。应该说,这些评价并非虚假的应酬之辞,而是发自心底的赞誉,至少是站在客观角度评价了新朝的治平气象。我们知道,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华夷之辨”,乃是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判断标准。当清廷接受并尊重汉民族文化之后,遗民原先的拒斥心理有所改观,也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受到这些开明政策的感召,李因笃虽然坚持不仕,却力劝友人积极进取:“盛代右文勤汉诏,茂陵车马莫踌躇。” “欣逢熙代崇儒术,竞许通才策茂勳。” 俨然已成为新朝的鼓手。
李因笃对新朝虽从拒斥变为接受,但其遗民底色仍顽强存留,这在他归乡后的诗文和行迹中都有鲜明体现。其《重叠前韵六首》云:“愿存贞秀性,同保岁寒姿。” 坚如磐石的遗民立场即此可见。抵家之后,他“随易常服,见宗族戚友,口不道京邸事,居家不改寒素风” 。这些行为固然出于安贫乐道的性情,但从中亦不难窥见其与清廷的心理距离。在返乡后不久,其母去世,但他守丧期满仍坚决不仕。他意欲最大限度地维护遗民形象的用心,于此也显露无遗。另外,在顾炎武等好友陆续去世之后,暮年的李因笃伤感不已:“比失赏音人,旋亡同志友。寥寥天地间,郁郁丧家狗。”“丧家狗”一语,盖谓遗民友人的逝世致使其丧失了心灵家园,生存的依托也漂浮无定所。语气沉郁悲痛,可见其内心深处对遗民形象的自我认同。同诗中,他对一己之立身亦有反思:“竟尔窃虚声,行藏终抱疚。生平禀薄尚,淟涊空搔首。” 夹杂着自责、自惭和遗憾,愧疚于未能彻始彻终地持守人生理想。在与友人信中,他又感慨道:“伤老大之相催,行藏之失据,徘徊永夜,时相泣下沾衣也。” 亦是悔恨与羞愧、伤感与无奈交织杂陈。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他参加考试以及后来的被授予检讨,都是难由自主的被动行为。面对朝廷的强权,他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似乎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但上引言论也反映出其遗民情怀与底色的顽强存留,这与对新朝圣主的赞颂美誉共存一身,体现出其晚年心态的复杂和多元。
三
李因笃的心态流变在博学鸿儒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同时的博学鸿儒科诸人,特别是那些深具遗民情结者,其心理世界变动的历程和最终特征与李氏不无相似,也反映出清廷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及其限度。
博学鸿儒科诏书下达之后,“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唯恐不与” 。但许多气节之士则拒绝应征,除了李因笃之外,像毛奇龄、严绳孙等人起初均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脱。易代之后,毛奇龄曾作诗明志:“人生有义分,各自为主臣。季布哭项羽,王蠋悲齐湣。鸟雀自有侣,毛发亦有伦。不观山谷间,尚有秦遗民。” 以忠于旧主的季布和王蠋自比。严绳孙出身明代官宦之家,祖父为明代刑部侍郎,父亲为副贡生,他在明亡后洁身自好,满足于山水田园之乐,并以陆机入洛自诫:“吾闻洛阳道,得丧齐相赴。君看车马间,尘衣变缁素。” 深以素衣“变缁”为戒。清廷博学鸿儒科考试诏书下达后,他们都受到地方官员的举荐,毛奇龄曾三上《辞徵檄揭子》,列举自己才学不副,老病疲弱,百般推辞。严绳孙也寄书京师友人,极力拒绝。在考试过程中,二人均刻意犯下低级错误,但最后均被授予职务。进入明史馆后,他们目睹新朝统治的崭新气象,又受到康熙的种种眷顾,于是开始大力称颂圣主明君,相关论调与李因笃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奇龄集中如《奉和扈从登封应制四首》、《午门谢恩恭纪》、《瀛台赐宴赋》、《汤泉赋》等,皆堆积称誉之词。他说:“甘泉徒有赋,未敢拟扬雄。” 隐隐以颂扬新朝的扬雄自比。严绳孙在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后,作诗揄扬上功,诗序云:“臣以草野蒙恩,备员侍从,外之不能援笔幕府,效飞书驰檄之用,内之亦未获登名山而颂功,以继七十二代之编录,情不自已,聊成短律。斯若厦成燕贺,候至虫吟,猥从诸臣之后,仰塵睿览。” 言辞之间,满是对自己才能薄劣的愧疚与遗憾,已寻觅不到昔日对宦途的惊惧与畏葸。与李因笃、严绳孙并称“四大布衣”的朱彝尊与潘耒,前者一度投身反清复明斗争,后者从学于徐枋、顾炎武等遗民,在被征时不无抵触:“枚马掞天才不少,因何搜采到岩中。” 但进入史馆后,他们均以报效新朝为职志。朱彝尊对自己被擢拔一等,授翰林检讨的经历津津乐道:“故事,翰林非进士及第与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职,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异数矣。”两年后,他又被选为日讲记注官,后来出典江南乡试,“拜命之日,屏客不见。将渡江,誓于神。入闱,矢言益厉” ,意欲以此报答康熙帝的赏识。潘耒劝勉同人徐釚说:“词林为文学侍从之臣,怀铅握椠,固其职事,不得以雕虫篆刻为嫌。至吾侪遭逢不世,以文学特见褒异者,尤宜早夜孜孜于是。” 被征初期的徘徊与犹豫不见踪影,以文章报国,黼黻盛世,已然成为他们心态的重要方面。
不过,上述诸人在某些场合又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厌倦馆阁生活,期望返归故乡的心绪。早在离乡之初,他们就有强烈的返归田园之念;而李因笃的离京,则推动了这一心态的发展。李因笃离京时,他们多作诗送别。对比李氏的刚强与坚韧,他们或表达钦佩之情,或流露出自惭心理。毛奇龄《送李检讨予养还山》曰:“人生有初服,亦欲奠所贞。何为坐拘牵,密志徒怦怦。”“视此三寸扰,何如一日闲。予有湖上业,滟潋通周官。思以隔一曲,未敢徼圣欢。” 意欲挣脱官场束缚。严绳孙《送李天生同年侍养归秦中》云:“李子抱明义,出处何轩然。既览千古迹,肯遗寸心愆。……余交苦不早,执义乃随肩。顾我无一长,弥悲已徂年。招提对尊酒,中心难尽宣。愧尔既非一,敢忘平生言。” 喟叹自己的出处难比李因笃,末尾之语则透露出两人似乎早有约定,而又与行藏有关。潘耒《送李天生回关中》谓:“羡君胆坚刚,壮君气勇决。……国士信无双,于此见奇崛。” 对李氏的胆识赞叹不已。其实,与李因笃不无相似,他们在效忠新朝的同时,内心的兴亡之感并未荡涤无余,稍有机会便有流露,特别是在与遗民友人唱酬之时;他们对旧国的思念拂之不去,只是表达的方式稍显隐晦而已。毛奇龄曾以滞留北方不得南归的庾信来自比:“岂不被显爵,亦既叨殊恩。无如慕乡井,惠好难重陈。生逢乱离世,老作异代身。江南草长时,回望情弥殷。枳橘岂秦产,夷齐本商民。一吟思归辞,泪下霑衣巾。” 并不贪恋新朝给予的政治待遇和物质恩惠,而以“商民”自居。严绳孙居京期间也惭愧于未能持守自好:“今日风尘浑丧我,漫将身世问乾坤。” 而愈到晚年,他们反思自身的出处时,愈不乏自责和内疚。毛奇龄为自己预作墓志铭中,就有“出处未明” 一语。朱彝尊则对黄宗羲说“予之出,有愧于先生” 。这些心绪的产生,大概还是浓厚的遗民情结使然。有论者指出,博学鸿儒归乡之后,从事著述与诗文创作,内心较为平和,但就上引诸人的言论来看,则其内心世界显然存有一丝不安与惶恐,并未真正做到平淡自适。
明清易代之初,士林中以遗民自居者为数不少,但随着清廷统治的逐步巩固,又面对困难窘迫的生存环境,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降心出仕,为新朝服务。对这一情形,黄宗羲曾感喟道:“年运而往,突兀不平之气,已为饥火之所销铄,落落寰宇,守其异时之面目者,复有几人?” 与此同时,清廷也不遗余力地网罗遗民,将其吸纳到体制中来,为我所用,进一步消泯其故国情怀。新朝进士韩菼观察到:“圣人方急才,如开八紘,尝访及山林草泽间侧席幽人如不及,而词臣之出者得迁故官,比比也。” 以博学鸿儒的征召为标志,清廷分化遗民的政策到达高峰,关于康熙帝此举的用心,正如孟森先生所谓:“一为消弥世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 就其实际成效而论,那些进入翰林院的遗民,无形中受控于体制,自不敢放言高论;而不愿就职的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也由激烈趋于缓和,如顾景星在考试后被允准返乡,就对“圣德包无外,天恩遂许初” 感激涕零,回乡之后,他又向友人自陈心愿:“太平乐事还堪赏,白首狂歌答圣朝。” 从表面上看,康熙帝虽未将他们成功地笼络到体制中来,却通过赐官与赐归等柔性手段,很大程度上收揽了人心,进一步树立并巩固了自身宽宏大量的开明形象,所得远远大于所失。应当承认,在世易时移,遗民逐渐接受新朝的情势下,清廷通过以博学鸿儒科考试为代表的种种右文政策,加速了遗民心理世界的蜕变,也进一步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但不能忽视的是,任何政策的效用总有其限度。特别是对那些年长而又亲历明清易代的李因笃等人而言,他们的遗民情结已然根深蒂固,自非外力在短时间内所能扫荡无余。他们虽也对新朝歌功颂德,甚至还有或隐或显的报效之志,但其对人生出处的考量,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基准。可见由传统所赋予的某些文化心理,自有其韧性与强度,并不能被政治强权彻底消除。而经历明清鼎革的士人,其心态的迁换更非干净利落,往往在新变之中夹杂陈迹。这也是审视其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重要前提。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4期
初审编辑:牛乐耕
责任编辑:李士环